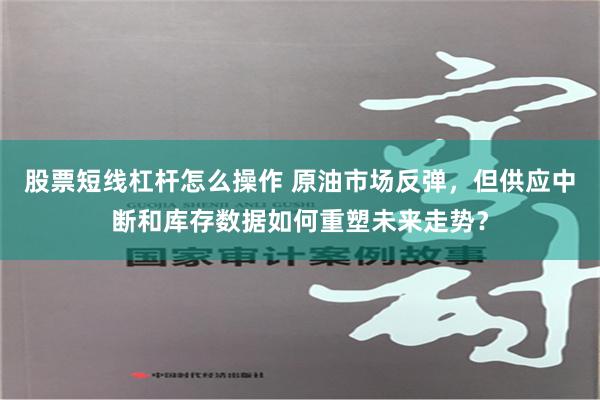知识嬗变与汉晋《左传》学的发展杠杆期货交易软件
文/方韬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韬副教授
摘 要 :汉晋是《左传》学从初创到成熟的关键时期。西汉末,谶纬与古文经并兴。东汉初,图谶成为官方学说。郑众引占候之术入《左传》,学者罕习。贾逵以图谶解传,为执政者赞赏,成为《左传》学发展的一大转机。汉末,今文经与图谶并衰,博物多识成为士人们的追求。服虔用《山海经》《神异经》解传,显示出其独特的博物趣味,而方言俗语的运用则与士林的旨趣同调。过度引入新知识,是服注繁琐的原因之一。在汉魏史学发展的背景下,杜预认为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为叙事之史。杜氏以其深厚的历法与地理学养,建构出全新的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时空知识框架,为后世《左传》学奠定了基础。
关键词 :《左传》;知识;谶纬,博物;史学;汉晋
《左传》是优美的历史散文,也是儒家经学的重要文献。儒家经学文献的核心是历代对经书的诠释。细究古人的注疏,不仅要留心注释者所欲解决的问题,考察其技巧方法,还必须重视其所凭借的知识学问。事实上,这些知识学问构成注疏的实体。注疏中有传承前贤的学问,也有注释者根据自己趣味增添的新知识。因此,知识学术的变迁深刻影响着经书诠释的发展。《左传》是篇幅最大的先秦典籍,可谓春秋时期的博物传记。汉晋是《左传》学从雏形初现到基本成熟的阶段。学者们将彰显个性又具时代特征的新知识引入阐释《左传》,有力推动了该学的发展。历代论述汉晋《左传》学者甚众,但多着眼于经传解释关系及今古文之争等问题,少有从知识史角度发掘汉晋《左传》学特点的研究。职是之故,本文不揣浅陋,以此切入,试图展现经典诠释与知识、时代的互动关系。
展开剩余94%一、谶纬之学与两汉间左氏学的废兴
西汉末期,经学学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。首先,在哀平与新莽时期,造作谶纬蔚然成风。自汉平帝元始五年开始,各种“符命”就络绎不绝。谶纬书的出现,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的篡位谋划有着密切的关系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云:“秋,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……其文尔雅依托,皆为作说,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。”王莽在奏疏中征引谶书,朝廷开始征召精熟谶纬的学者,意味着这一新学得到官方认可,那么“谶书在元始五年至新莽时期对经学的影响,一定大于同时期的经学对谶书的影响”。其次,与谶纬兴起近乎同时,古文经《左传》《周礼》也在王莽时代受到重视。《周礼》虽得到刘歆重视,但却是在王莽以周公为号召,复古改制的过程中逐渐被发掘出来的。刘歆中秘校书时发现《左传》古本进而大力提倡。作为战国古文字书写的文本,《左传》传习者首先要解决大量文字训诂的问题,因此汉初以来“学者传其训故而已”。是时,《公羊》是官方认可的《春秋》学说。刘歆充分借鉴《公羊》学的阐释方式,引《左传》解《春秋》,于是左氏“义理章句备焉”,始与《公羊》争胜。
▲《春秋左传杜林善本》(清代文盛堂刊本)
那么,左氏学与谶纬有无关系?作为斯学的开山宗师,刘歆深信谶纬。改名刘秀,是为了应《赤伏符》“刘秀发兵捕不道”之谶。无论是西汉末的政治阴谋家想借助刘歆的宗室身份推翻王莽,还是自己有非分之想,刘歆都与谶纬有密切的关系。《王莽传》记载地皇四年前后,道士西门君惠据“天文谶记”指出:“星孛扫宫室,刘氏当复兴,国师公姓名是也。”国师公即刘歆。可见,西汉末谶纬与古文经两股学术洪流汇聚其身。不过,谶纬在刘歆的左氏遗文不见踪迹。
王莽、刘歆未能成功的图谶游戏,在光武帝手里大放异彩。《赤伏符》提到刘秀之名,群臣以为是受命之符,光武帝被拥戴即位皇帝。于是,建武中元元年刘秀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,遂成为官方推重的理论学说。谶纬涵盖占候与图谶,但细分两者仍有较大差别。风角等占术是“依据一定的理论和方法,以自然或人为现象为出发点进行推算”,而“谶纬中却有大量不经过‘占’得出的预言”。尽管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,但占候要按一定规则来进行推算,意味着有相当的理据与规范。图谶则服务政治,随意性很大。不少学者不信图谶。张衡《禁绝图谶疏》集中表达了图谶效用不如占候之术的思想,并明言:“天文历数,阴阳占候,今所宜急也。”尽管身处热衷图谶的光武朝,左氏先师并未像刘歆那样接受这套未经推算的学问。桓谭《新论》认为谶纬非圣人所作,颇多虚妄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桓氏因不读谶激怒光武帝,险些失去性命。《郑兴传》云:“兴数言政事,依经守义,文章温雅,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。”因此,左氏学很难得到当政者支持。
《左传》在光武朝未被立于学官,但经刘歆的弟子郑兴、贾徽及二氏之子郑众、贾逵发扬光大,成为贾郑之学。贾郑学虽源于刘歆,但各具特色。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曰:“尝欲训《左氏春秋》,及见贾逵、郑众注,乃曰:‘贾君精而不博,郑君博而不精;既精既博,吾何加焉’。”马融指出,贾、郑《左传》注的特点:贾氏注精而郑氏注博。郑众注存世者仅六十余条,今举一例以见其博。《左传》僖五年:“五年,春,王正月辛亥朔,日南至。公既视朔,遂登观台以望,而书,礼也。凡分、至、启、闭,必书云物,为备故也。”《左传正义》引郑众注云:“以二至、二分观云色,青为虫,白为丧,赤为荒,黑为水,黄为丰。”青、白、赤、黑、黄为五色,郑注中除黑为水外,其他解释非五行之说,当有其他来源。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云:“众之此言盖出占候之书,计云气之占不啻尽此而已,但世绝其学,故莫能知焉。”唐初孔氏尚能见郑众注,知其为云气之占,但谶纬之书历经南北诸朝并隋代两帝的严禁,孔氏已不能明其占术。事实上,望气占候之术渊源甚早,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:“以五云之物,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。”郑玄注:“物,色。视日旁云气之色。”而僖五年《左传》也正记载鲁国有登台观气之礼。其他诸侯国也有观象台。这套占气之术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,日趋精密。
不过,风角占候这些知识资源引入《左传》,并未得到多少《左传》学者的响应。上文提到《左传》僖五年,《太平御览》卷8引汉儒旧注曰:
启,立春夏也,阳气用事为启。闭,立秋冬也,阴气用事为闭。云,五云也。物,风、日、月、星、辰也。分、至、启、闭,天地之大节,阴阳之分也。故遂登观台望气,以审妖祥变乱之气,先见于八节,书其云物之形,言其所至,务为之备也。
此注涉及望气,但未言占术。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认为其注当为贾逵服虔。杜预与之无大差异,惟去其阴阳之说而简化之:“启,立春、立夏。闭,立秋、立冬。云物,气色灾变也。”可见,贾逵、服虔、杜预之注与郑注皆不同。而且,贾注、服注今皆有数百条辑存,然无一则言及占候之术。可稍作推论,不惟孔颖达不解占候之术,很可能与郑众同时的贾逵亦不以占候解经。
▲刘文淇等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3年)
贾逵引图谶入《左传》,却为左氏迎来生机。此举意图,公羊学者看得分明。何休《公羊序》云:“至使贾逵缘隙奋笔,以为《公羊》可夺,《左氏》可兴。”何休为何只言贾逵不提郑氏呢?徐彦《公羊传疏》解释道:“郑众亦作《长义》十九条十七事,专论《公羊》之短,《左氏》之长,在贾逵之前。何氏所以不言之者,正以郑众虽扶《左氏》而毁《公羊》,但不与谶合,帝王不信,毁《公羊》处少,兴《左氏》不强,故不言之。”可见,郑众攻击《公羊》提振《左传》虽在贾逵前,但其不用图谶,当政者不信,故左氏学不得大兴。而贾逵上疏汉章帝云:
臣以永平中上言《左氏》与图谶合者,先帝不遗刍荛,省纳臣言,写其传诂,藏之秘书……至光武皇帝,奋独见之明,兴立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,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,故令中道而废……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,而左氏独有明文。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,而尧不得为火德。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,即图谶所谓帝宣也。如令尧不得为火,则汉不得为赤。其所发明,补益实多。
贾逵认为《左传》有明文证明汉为尧后,正可与图谶印证发明。《左传》文十三年有晋士会留在秦国的后代为刘氏,所谓“处者为刘氏”,而襄二十四年鲁叔孙豹答晋范宣子、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献子皆提到刘氏祖先刘累为陶唐氏帝尧之后。因此,贾逵将图谶之学引入《左传》,立刻得到了汉章帝的欣赏:“帝嘉之,赐布五百匹,衣一袭,令逵自选《公羊》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,教以《左氏》,与简纸经传各一通。”此举极大提高了《左传》学的地位。
郑众、贾逵皆受学于杜子春。但贾氏学行于世,而郑说不行,恐怕亦与图谶有关。《序周礼废兴》云:“众、逵洪雅博闻,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,逵解行于世,众解不行……然众时所解说,近得其实”。贾逵、郑众的治经方法相近,都注重对经书的发明。但在东汉官方加持图谶的氛围下,尽管郑众的解释更切实,但引入图谶的贾逵经说是利禄之途,成为吸引经生的关键。对于左氏先师的命运,范晔的评论很精彩:“桓谭以不善谶流亡,郑兴以逊辞仅免,贾逵能附会文致,最差贵显。”可见,在东汉的时代背景下,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经说,很难脱离时代主流政治学说的影响。
杜预回顾《左传》这段学术史:“然刘子骏创通大义,贾景伯父子、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”,不及郑氏。的确,《左传》在两汉的勃兴,与刘歆、贾逵关系密切,尤其二氏引入时代主流政治学说对《左传》兴起的影响。刘歆借鉴《公羊》学创立了《左传》的解经理论,贾逵引入图谶复兴《左传》,都是关键因素。不过,占候与图谶都非《左传》文本中的固有知识。随着经学的发展,那些缺乏体系建构,远离经文本身的知识渐趋消亡。郑众注占候之学今仅一条,贾逵注中图谶之说荡然无存。
二、博物多识与汉末《左传》学的趋向
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,东汉后期今文经学与图谶都没落了。官学废弛,私学复兴。这时期诸子学兴起,士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。摆脱了旧知识体系的束缚,士人们对异方异物的兴趣大增,实开魏晋博物学的新风。据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所开列的书目可知,所谓博物之学主要包括两类:“一类是以《山海经》《禹贡》为代表的山川地志,一类是《尔雅》《说文》为代表的小学著作。”由此,汉晋人理解的博物学应是“方士探索异域的方物之学与儒士训诂名物的多识之学”。而这两类知识被汉末左氏学者熔铸于经书的注解中。
作为地志方物渊薮的《山海经》格外引人瞩目。学者认为“它集异域、异人、异物、异俗、异术之大成,为中国博物学奠定基本色调”。或许其书的博物特点也导致了古人对其性质判断的困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山海经》列在“术数类”下“形法家”,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,唐宋史志多同之。清儒编《四库全书》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。显然历代对《山海经》性质的认知差异巨大。
从先秦文献对《山海经》的接受来看,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吕氏春秋》诸书都可能援引《山海经》。退一步,至少也说明这些典籍有共见的知识资源。不过,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明言:“言九州山川,《尚书》近之矣。至《禹本纪》《山海经》所有怪、物,余不敢言之也。”尽管汉代诗赋家大量征引《山海经》是不争的事实,但司马迁的审慎或许更能代表学者的态度,在汉末经子要籍注释中,极少有人引入《山海经》。
郑玄遍注群经,但未引《山海经》为注。前文提到,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与《山海经》关系密切,年辈晚于郑玄的高诱也不引其注书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:“肉之美者,獾獾之炙。”高注:“獾獾,鸟名,其形未闻。”高诱指出獾獾为鸟。而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有鸟名“灌灌”,其文云:“有鸟焉,其状如狐而九尾,其音若呵,名曰灌灌,佩之不惑。”故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指出,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之“獾獾”“即此鸟也”。尽管两者音义相通,但高诱不引《山海经》而阙疑,可能《山海经》未进入高诱的视野,或碍于内容的荒诞而弃之。
▲《山海经》(和刻文光堂藏本)
作为地志神话渊薮的《山海经》,与记载春秋史事的《左传》内容关联度不高,远不如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。那么,东汉左氏先儒很可能也不引《山海经》注《左传》。不过,这一切在服虔《春秋左氏传解谊》中发生了变化。服氏不仅引《山海经》,还引性质相同的《神异经》为注。这些广记异物的博物书籍极大拓宽了《左传》诠释的知识边界。
服虔用《山海经》注《左传》,改变了《左传》名物的性质。《左传》文十八年有浑敦、梼杌、饕餮,先儒认为三者为形容词,意在凸显不德之人的某种品格。据《左传》文十八年“昔帝鸿氏有不才子,掩义隐贼,好行凶德;丑类恶物。顽嚚不友,是与比周,天下之民谓之浑敦”来看,无论帝鸿之不才子还是高阳氏的才子八恺、高辛氏的才子八元皆为上古君王之子。杜预认为,帝鸿氏不才子是“驩兜”,并指出:“浑敦,不开通之貌。”驩兜为舜所流放,事见《孟子·万章》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等。不过,《左传正义》云:“服虔用《山海经》,以为驩兜人面马喙,浑敦亦为兽名。”驩兜、浑敦皆为怪兽,与《左传》本文相去较远。“驩兜人面马喙”,今本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作“驩头人面鸟喙”,“驩兜”即“驩头”,“马”疑为“鸟”之误。服氏据《山海经》将《左传》中的上古人物引向了神异的世界。
浑敦为兽名,于《山海经》无征。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指出“浑敦亦为兽名”出自《神异经》。“梼杌”,贾逵认为是鲧,“梼杌,顽凶无俦匹之貌”。服虔以为是怪兽。《左传正义》云:“服虔案《神异经》云:梼杌状似虎,毫长二尺,人面虎足,猪牙,尾长丈八尺,能斗不退。”这种注释方向完全从名物角度考察,已偏离了《左传》的语境,是个人知识趣味的体现,故为后世注家所不取。
服虔对《春秋》异物的解释别于先儒,也可能得益于《山海经》《神异经》。汉儒多用灾异说《春秋》。但对于为害的异物,服虔之解异于《汉书·五行志》。《左传》庄十八年云:“秋,有蜮为灾也。”服虔注:“短狐,南方盛暑所生,其状如鳖,古无今有,含沙射人入皮肉中,其疮如疥,遍身中濩濩蜮蜮,故曰灾。礼曰:惑君则有。”令人疑惑的是,蜮已见于《春秋》,服虔为何认为古无而今始有,又据之注《左传》呢?按《汉书·五行志》:云“严公十八年‘秋,有蜮’。刘向以为蜮生南越……蜮犹惑也,在水旁,能射人,射人有处,甚者至死。南方谓之短弧,近射妖,死亡之象也……刘歆以为蜮,盛暑所生,非自越来也。” 颜师古注:“以气射人也。”据《五行志》可知,蜮盛暑所生,南方谓之短狐,以气射人。然而,蜮的形貌如鳖,射人生疮如疥等,服注所述与《五行志》颇为不同,或得益于博物之书。而杜预就简略谨慎得多:“蜮,短狐也。盖以含沙射人为灾。”
如果说,服虔在地志方物知识上的援引异于同侪,那么在名物学上的知识就与士林同调了。“名物学与专门解释文字音义的小学密切相关”。这些名物不仅关乎小学训诂,还往往涉及地方的风俗逸事。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记载了许多地方的风俗异事,曹道衡甚至指出其与魏晋六朝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应旸传》裴松之注引华峤《汉书》曰:“子劭字仲远,亦博学多识,尤好事。诸所撰述风俗通等,凡百余篇,辞虽不典,世服其博闻。”应劭所谓“好事”者,事即故事,包括典章制度掌故,还有方俗逸事。而这些事不见于经传,故辞不雅驯,华峤说其“辞不典”。不止应劭,杨天宇指出,郑玄常用方俗俚语解经。三《礼》注“引汉制、汉俗等以释古制”,“还有以汉之俗字、俗语、方言等释经字、经义者”。服虔出身贫寒,“少年清苦励志”,与应劭等儒家大族不同。服氏撰《通俗文》一书,“是我国第一部专释俗言俚语、冷僻俗字的训诂学专著”。由此可见汉末士人的共同趣味。服虔将这些方俗俚语也渗透到《左传》注释中。
服虔习用当时俗语类比以解经。经书庄重,服虔注经却不避詈言。《左传》僖二十八年:“楚子伏己而盬其脑”。杜注:“盬,啑也。”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疏证道:“盬之为啑,未见正训,盖相传为然。服虔云:如俗语相骂云:‘啑女脑矣’。”孔氏认为杜预的训释无据,而服虔用俗语类比解经,也非直接训释。需要指出,服氏将世俗詈言引入经注,为先儒所无。杜预可能认为经书训释不应有詈言,故删去。杜训盬为啑,视为直训,但为清儒诟病。服氏有时用本地俗语。成二年《左传》成二年:“若苟有以借口而复于寡君。”《左传正义》引服虔云:“今河南俗语,治生求利,少有所得,皆言可用藉手矣。”服虔河南荥阳县人,故用其本地俗语。清儒李贻德指出“服引俗语藉手以明借口之义”,实质也是古今之间的类比解释。故杜预注“藉,荐。复,白也”,弃其俗语不取。
▲《春秋左传正义》(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)
就解经而言,服虔所引俗语,意义并不大。《左传》宣四年:“子公之食指动”。《左传正义》引《礼仪·大射礼》“设决朱极三”郑玄注:“极,犹放也。所以韬指,利放弦也,以朱韦为之。三者,食指、将指、无名指。小指短不用。”可见,郑玄指明中间三指中第一为食指。若从拇指开始计数,则如服虔注:“第二指。”不过,服氏此后还有解释:“俗所谓啑盐指也。”事实上,前者已清楚明了,后者用俗语补充有蛇足之嫌。
要之,服虔引进博物学的注释资源,形成了与先儒颇为不同的诠释。但是,新知识引入过多也造成了服注的繁复。孔颖达僖《左传正义》僖十五年委婉批评道“服虔其文甚烦”。魏晋学术推崇精要,杜预大量简化服注,刊落这些博物学的内容。因此,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不言服虔之名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三、史学转向与西晋《左传》学知识的重建
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是《左传》最重要的古注,与《春秋释例》一起构成《左传》杜氏学。仔细研读杜注可知:郑氏占候之学、贾氏图谶之学、服氏博物之学在杜注中皆无踪迹。换言之,杜预将其逐出自己的《左传》学领地。从知识史角度来看,汉注到杜注是一次重大变革。如何理解杜氏构建的新《左传》学呢?
根本上讲,这一变化可归结为汉魏史学的发展。汉末天下大乱,诸侯纷争,如何汲取历史智慧来应对这一变局为当务之急。胡宝国指出:“从汉魏之际开始,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。”史学的发展促成了杜氏《春秋》观的转变。汉儒认为《春秋》是寓有孔子褒贬微言的圣典。但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开篇云:“《春秋》,鲁史记之名也。纪事者,日以系月,月以系时,时以系年。所以记远近,别同异也。”杜氏对《春秋》的定性是鲁国记事之史。在其看来,孔子并未彻底改变《春秋》性质,仅做了若干修订工作。清儒皮锡瑞谓杜预此说为“经承旧史”。
从知识史角度理解这种转变,就应当重视阐明杜氏《左传》学框架的《春秋释例》。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曰:“又别集诸例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,相与为部,凡四十部,十五卷,皆显其异同,从而释之,名曰《释例》。”可见,《春秋释例》主要包括了四类知识:《左传》义例、春秋地名、谱第、历数。除去属于《春秋》经学核心范畴的义例外,地名、谱第、历数皆在史学。观辑本《春秋释例》可知,《土地名》主空间,《经传长历》主时间,而《世族谱》主人物。这就构成历史叙事的三要素。我们从时间、空间两维度看杜预注释《左传》在知识史上的变化。
在汉代《春秋》学中,时月日例是《公羊》《谷梁》的核心义例。二传以为,《春秋》中的时、月、日皆体现圣人的褒贬大意,与叙事时间无关。清代《公羊》学家刘逢禄著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》十卷,有例三十,其中“时月日例”部
最大,分一卷。刘师培著《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》,另《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》有“时月日篇第十二”,认为汉儒以时月日例说《左传》。左氏先儒刘歆、贾逵、许淑、颍容等皆以时月日为例。隐二年《春秋》:“十有二月乙卯,夫人子氏薨。”《春秋释例·崩薨卒例》引先儒刘贾许颍曰:“日月详者吊赠备,日月略者吊有阙”。先儒认为《春秋》日月详细的,是由于丧礼齐备不阙,而日月略者则是吊礼有阙。而夫人丧礼有阙,则圣人有所讥刺。《春秋》文八年:“公孙敖如京师,不至而复。丙戌,奔莒。”《春秋释例·大夫卒例》引贾逵曰:“日者以罪废命,大讨也。”公孙敖受君命如京师,但未成君命而返国,又出奔莒国。贾逵认为《春秋》书“丙戌”以见其以罪废君命,宜国大讨。据此,《春秋》当极贬公孙敖。在左氏先师看来,《春秋》书时月日的确寓有圣人褒贬微言大义。
那么,杜预如何应对呢?《春秋》隐元年:“公子益师卒。”杜预注:“《春秋》不以日月为例,唯卿佐之丧独记日以见义者,事之得失,既未足以褒贬人君,然亦非死者之罪,无辞可以寄文,而人臣轻贱,死日可略,故特假日以见义。”杜氏明确指出《春秋》无以“日月”为例者。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阐扬杜说:“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书,道听途说之学,或日或月,妄生褒贬。先儒溺于二传,横为《左氏》造日月褒贬之例,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。”杜预反对时月日例,认为时月日不过是计度时间的单位,与《春秋》的褒贬微言无关,而在于明叙事。正如《春秋长历》云:“四时八节无违,乃得成岁,其微密至矣。得其精微以合天道,则事叙而不悖”,杜氏在汉魏历学的基础上重新推定春秋历日,以叙事时间来定义春秋历日是杜预在《左传》学知识的一大拓展。
▲杜预像(故宫南薰殿旧藏《至圣先贤半身像册》)
先儒刘歆创制《三统历》,贾逵参与后汉《四分历》的修订,都是精通历学的大师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云:“向之子歆究其微眇,作《三统历》及《谱》以说《春秋》……夫历《春秋》者天时也,列人事而因以天时。”在刘歆看来,历者天时也,那么历法首先要合乎天。《春秋》依据天时而具列人事。由于历术追求合于天,那么当《三统历》与《春秋》经传历日产生矛盾的时候,刘歆通常倾向于《三统历》而非经传。同理,象征天时的时月日就被汉儒赋予了神圣意义,刘歆贾逵承认时月日例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汉儒据《三统历》《四分历》来推算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历日,往往与经传的记载差异较大。刘歆就改动了《春秋》经传近乎所有的日食之期。郜积意指出,刘氏改动的原因在于据三统术推算以日食干支日为目标,而对其确切日期并不措意。为解决这一矛盾,杜预以经传历日为基准推算,所谓“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、日食以考晦朔也”。换言之,《春秋长历》的编制如郜氏所言“不全依历理”,“其目标不是为了合天,而是为了合乎经传”。那么,杜预实质上在天人之间作了选择,以人事为要。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指出,日月时年不过是区别叙事的时间,“纪事者,日以系月,月以系时,时以系年。所以记远近,别同异也”,所以《春秋长历》编制的目标也当是服务于经传叙事。
因此,《春秋长历》将经传的干支纪日皆转换为序数纪日。譬如,《左传》昭二十四年:“三月庚戌,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。”《春秋长历》云:“三月庚戌,十五日。”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所秉干支纪日,这是商代以来的纪时传统。不过,这种纪日方式在秦汉时期发生了变化。有学者认为,至迟在西汉武帝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都已有序数纪日的记录。延至汉末魏晋,在民间序数纪日逐渐成为强大的传统。甚至将“上巳节”与“端午节”本按干支日确定的节日,重新用序数纪日确定在“三月三日”与“五月五日”。事实上,变干支为序数显然更便于民间的记事。
不过,我们发现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中,并非所有干支纪日皆注以序数,而是少数经传历日无法与《长历》协合时,杜预才据《长历》说明经传之误。譬如,《春秋》隐二年:“秋八月庚辰,公及戎盟于唐。”杜注:“八月无庚辰。庚辰,七月九日。日月必有误。”用《长历》推定庚辰在七月第九天,继而判断《春秋》或是庚辰日误,或是八月误。魏晋时期无论是官修史抑或私修史,体例皆依《春秋》用干支纪日。而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不皆用序数也可能是杜预对传统的遵循。
《春秋长历》是杜预《左传》学的重要构成,也是其研治经传的锐利武器。笔者统计,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指摘《春秋》《左传》谬误者53则,其中历日误者竟有41则。与郑玄服虔这些擅长小学的经师不同,杜预极少用小学解决经传的文字讹误。从历日入叙事考辨文本谬误是杜氏的重要方法。试举杜注中最著名的文本考订例。
▲《春秋经传集解》(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本)
《左传》襄九年:“十二月癸亥,门其三门。闰月戊寅,济于阴阪,侵郑。”杜预注:“以《长历》参校上下,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。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。疑‘闰月’当为‘门五日’。‘五’字上与‘门’合为‘闰’,则后学者,自然转‘日’为‘月’。晋人三番四军,更攻郑门,门各五日,晋各一攻,郑三受敌,欲以苦之。癸亥去戊寅十六日,以癸亥始攻,攻辄五日,凡十五日,郑故不服而去。明日戊寅,济于阴阪,复侵郑外邑。阴阪,洧津。”对于自己的考论,杜预在《春秋长历》中显得相当自信:“于叙事及历皆合。”需要指出,杜氏强调叙事,显然这番考证是综合叙事与时间、空间等因素的,绝非单纯的历日推算。
杜氏先据《春秋长历》判断此年不当有闰月戊寅。依《长历》,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,传文前有“十二月癸亥”,那么《左传》“闰月”误。癸亥到戊寅共十六日。结合前文“门其三门”,三门每门攻五天恰好分配十五天。因此,杜预认为晋国集中四军攻一门,三次攻不同城门,让郑人疲于防备。因此,闰月当为“门五日”。但郑不服,晋军遂于戊寅日渡过洧津侵郑。再从字形看,闰字可能是门五两字合书之误,闰日不成词,后人遂据闰改日为月。从军事上讲,兵力与时间的分配皆随战局应时变化,均分十五天显然不太可能。但在理论上,杜预还是实现了叙事与时间(十五日)与空间(三门)较合理的结合,最后从字形讹误上找到原因。应该说,这是利用历史学知识来解决文本问题。尽管南北朝诸儒对杜氏的推论颇有诘难,但今人杨伯峻仍表示肯定。
杜氏对《左传》学知识另一拓展在地名。汉魏史学发展刺激了对地理知识的探求。不过,这种兴趣在《左传》学中是渐进的。汉代《春秋》学中有书地之例。《春秋》隐十一年:“公薨”。《公羊传》云:“弑也。不地,不忍言也。”《公羊》认为《春秋》不书鲁隐公薨于何地,是由于隐公被臣子弑,圣人有不忍之心。显然,此处对书地名的解释并非客观叙事的需要,“不忍言”是诉诸主观情感的行为。刘逢禄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》有“地例第二十六”,刘师培《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》有“地例第十五”,皆为明证。
汉儒对春秋地名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。汉代《公羊》家多不注地名,有注者也甚简。譬如,《春秋》庄二十二年:“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。”何休注:“防,鲁地”。只简单交代了古地当时的国别。贾逵注《左传》与之非常相似。隐元年《左传》:“请京,使居之。”贾逵注:“京,郑都邑。”昭二十三年《左传》昭二十三年:“王师在泽邑。”贾逵曰:“泽邑,周地也。”这说明贾氏并未意识到,面向当时士人的经注,春秋地名需要释为今地。在贾逵的时代,这些内容并不属于经注的范畴。延至汉末,服虔《春秋左氏传解谊》有了些新变化。《左传》僖二年:“灭下阳。”服虔注:“下阳,虢邑也,在大阳东北三十里。”《左传》定十年:“夏,公会齐侯于祝其,实夹谷。”服虔注曰:“东海郡祝其县也。”以上春秋古地名都落实到东汉的郡县,有的还指出所处方位。这些郡县名近于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而远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是西晋司马彪撰,服虔则有可能参考了诸如《东观汉记》之类史籍中的地理志。这类地名注释体现的空间观念已具有史学的特点。不过,这些注文条目甚少,难称服注《左传》地名的主流。与之相近,汉末高诱《吕氏春秋》注、《淮南子》注,甚至三国韦昭《国语》注中也有类似的地名注,可见汉末地理知识在士人中的影响。
▲东汉《公羊传》砖(东汉元和二年刻)
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《春秋释地·土地名》都尽量将春秋古地名落实到西晋郡县。华林甫《中国地名学源流》指出:“与班固、应劭不同,杜预以释出今地为主,于地名五大要素中偏重于‘位’这一项,即定位研究。”位即地名所代表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,包括方位和空间范围。譬如,《左传》僖二十四年:“济河,围令狐,入桑泉,取臼衰。”杜注:“桑泉在河东解县西。解县东南有臼城。”杜注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两个古地在今的大致方位。“杜预对1000多处地名作了研究,因而对地名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。”如同《春秋长历》,杜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春秋古地今释体系。
作为军事家,杜氏曾在西北抗击匈奴入侵,随钟会伐蜀,后主持伐吴。其对空间地理的理解与经师儒生有着本质的差异。伐吴中与王濬书:“足下既摧其西藩,便当径取秣陵,讨累世之逋寇,释吴人于涂炭。自江入淮,逾于泗、汴,溯河而上,振旅还都,亦旷世一事也。”显然,他对当时的军事地理如运指掌。因此,杜预对地名有独特的理解:“然详而究之,非书无以志古,非图无以志形。坐于堂宇之内,瞻天下之广居,究古今之委曲,可以行,可以言,可以鉴,可以观,多识山川分野之别,贤愚成败得失之迹,虽千载之外,若指诸掌,图书之谓也。以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,山川道途之实,爰及四表,自人迹所逮,舟车所通,皆图而备之。然后以春秋诸国邑,盟会地名各所在,附列之,名曰古今书春秋盟会图。”杜氏强调治地理必须由书以考古,据图以查形。尤其注意到古今郡国县邑之名与山川道途实际地形的不同,尤为可贵。因此,其注释地名中有对实际地形的描述。《左传》僖三十二年写到崤之战蹇叔谈崤之地势:“崤有二陵焉:其南陵,夏后皋之墓也;其北陵,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”杜预注:“此道在二崤之间南谷中,谷深委曲,两山相嵚,故可以辟风雨。古道由此。魏武帝西讨巴汉,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。”所谓“谷深委曲,两山相嵚”乃崤地之实际形貌,若非亲身经历则不能道。而曹操西征巴蜀,惧其险阻另辟新道,则指出其地势险要,流露出其军事家的识见。
在《春秋释例·土地名》中,杜预对古地名的研究往往在叙事的背景下综合时间与空间,超越了简单的地名考证。《春秋释例·土地名》:“(襄)十年,柤:阙。或曰:彭城偪阳县西北有柤水沟。鲁国薛县西南有柤亭。谯国酂县治戏乡。皆去钟离五百余里,非诸侯六日载会所至也。或曰:汝南安城县西南有钟离亭。西平县北有柤亭,去偪阳近千里,又非自会九日之所能灭国,皆非也。”柤这个古地名见于《春秋》襄十年:“十年,春,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、齐世子光会吴于柤。”杜注:“柤,楚地。”由于不知其今地所在,杜注“楚地”与《春秋释例·土地名》“阙”是一致的。而当时对“柤”之今地有种种说法,但杜预逐一驳斥,最终阙疑。
杜氏的考据值得品味。从地名的命名上考虑,一说彭城偪阳县西北有柤水沟,一说鲁国薛县西南有柤亭,一说西平县北有柤亭,其中皆有关键字“柤”,的确可能与古地名“柤”相关。《左传》襄十年写道:“三月,癸丑,齐高厚相大子光,以先会诸侯于钟离,不敬。”“夏,四月,戊午,会于柤。”杜预据《长历》确定三月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,而四月戊午是四月一日。两会仅隔六日。杜预将假设的地名带入《左传》叙事中,钟离今地可确定在淮南县,因此上述三地离淮南县五百余里,六日内无法到达。又说,汝南安城县西南有钟离亭,与古地名“钟离”合。西平县北又有柤亭,名合于“柤”。然《左传》襄十年后文写道:“晋荀偃、士匄请伐偪阳,而封宋向戌焉。荀罃曰:‘城小而固,胜之不武,弗胜为笑。’固请。丙寅,围之,弗克。”杜预注:“丙寅,四月九日。”偪阳可知在彭城传阳县,而上述两地距此皆近千里。柤之会在四月一日而围偪阳在九日,晋军九日内赶到围国而灭之,显然不可能。可见,杜预注释地名时,是将其置于《左传》的历史语境中,综合时间、空间与历史叙事来辨明是非。
应该说,杜预《春秋释例·土地名》是经过自己反复考校后建立的地名体系,与其《春秋长历》一起构成了解读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历史叙事的时空坐标。辅之以《春秋世族谱》,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叙事要素的知识体系。再结合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义例,应该说,杜预为《左传》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知识框架,对后世影响极深远。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的。
小 结
汉晋《左传》学发展历程中,《左传》解经理论的建立最受关注。不过,《左传》内容鸿富,注家云集,从知识变迁的角度考察《左传》古注很有必要。西汉末学术丕变,谶纬与古文经学成为新趋向。刘歆借助《公羊》学阐明《左氏》,但其谶纬却未在左氏学中留下痕迹。光武帝登基后,图谶成为官方学说。郑兴郑众引风角占候之学解传,但不言图谶,不得世主欢心,其学不显。贾逵引入图谶说经是东汉左氏学振兴的重要原因。汉末中央王朝没落,今文经学与图谶并衰。失去思想束缚的士人们知识趣味多元化,博物多识是其中重要的趋向。服虔引《山海经》《神异经》等注《左传》,与经文文本关涉不大,是其博物趣味的独特体现。同时,喜用方言俗语则是汉末士林博物多识的共同旨趣。大量新知识引入,造成了服虔注的繁琐。异于汉儒,杜预认为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本质是叙事之史。在建构经传义例外,杜氏以历史叙事为中心,建构了庞大的知识体系。杜氏摒弃了用历谱推算春秋历日的旧法,在尊重经传叙事的基础上,以经传所记历日为基准,编制《春秋长历》。杜预用便于记事的序数纪日解释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干支纪日,并将《春秋长历》作为解决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文本问题的一把钥匙。而《土地名》竭尽可能地以今地释古地杠杆期货交易软件,并绘制了《春秋盟会图》。因此,杜预建立起全新的理解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时空知识体系,为后世的《左传》学奠定了基础。
发布于:黑龙江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联华证券策略_专业杠杆炒股公司_正规杠杆炒股平台观点